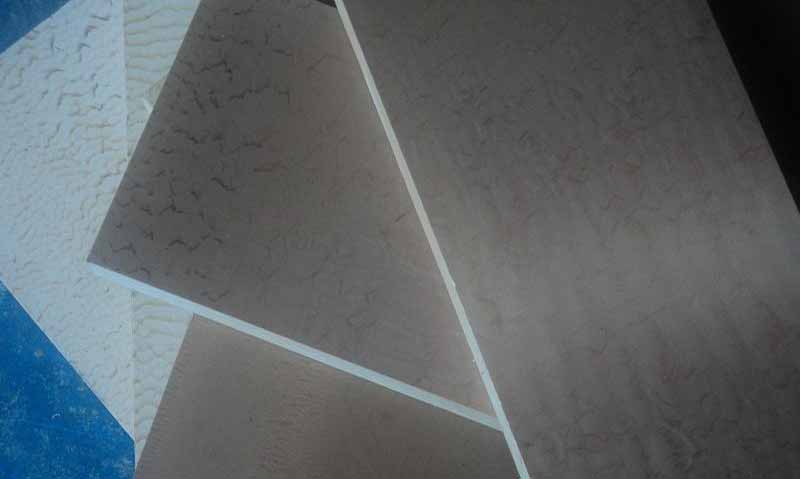
近年來,3D 打印在醫療行業的使用比例持續增長,產品也逐漸獲得了監管機構的批準。這主要是因為醫療行業(尤其是修復性醫學領域)的個性化定制需求顯著,且鮮有標準的量化生產,而這恰好是3D打印技術的優勢所在。
傳統醫療常見的處理方式是根據病人的臨床癥狀和體征,結合性別、年齡、家族疾病史、實驗室和影像學評估等數據確定藥物和使用劑量、劑型,而這種醫療模式正在悄然發生變化。近年來,我們常常會聽到個性化醫療(又稱精準醫療)這一名詞,這是一門與傳統醫療截然不同的定制醫療模式。隨著輔助制造行業的快速發展,尤其是3D打印技術的大發展大繁榮,或將顛覆傳統醫療模式。
目前,生物3D打印雖然應用范圍廣泛,但仍以研發需求為主,暫時難以面向消費市場,且存在著行業壁壘較高、上下游產業鏈尚未成型、監管政策和行業標準幾近空白等問題。
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國家“青年千人計劃”專家劉靂宇的研究方向之一是高精度生物材料3D打印技術、3D微流體生物芯片先進設計與加工,對于生物3D 打印有著自己的見解。近日,記者與劉靂宇近距離對話,以期通過他的視野了解當前生物3D打印的發展現狀和重難點,為生物3D 打印和個性化醫療未來的發展提供新思路。
生物3D打印在中國
記者:在國際大背景下,目前生物3D打印的發展現狀是怎樣的?
劉靂宇:當前,生物3D打印主要應用在兩個方面——第一類是面向生物醫學的3D打印技術,這是目前市場發展應用的主流,基本上占90%以上。它主要是協助醫療機構進行手術和康復服務,比如打印義肢、心臟、肝、腎等模型,醫生可以在做手術的時候對照這些模型,進行一些復雜的手術。這一方面,近兩年在我們國家發展得如火如荼,應用也很有彰顯力,具有很大的市場前景。但是,我認為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物3D打印。
我理解的真正意義上的生物3D打印指的是后者——基于生物體的3D打印技術,面向植入生物體的生物兼容性材料,或者以細胞為材料的打印技術。這是3D打印技術發展最前沿的方面,也是目前積極研究、重點攻克的方面,如果研發成功,其意義和價值是非常巨大的。這可以代表生物3D打印未來幾十年發展的主要途徑。因此,也是最困難、最有挑戰性、卻是在未來最有影響力的研究。
記者:那么,在生物3D打印的兩個應用領域中,我國目前主要發展的是哪一方面?其應用處于哪一階段?
劉靂宇:在我國目前第一類的3D打印技術,針對于輔助醫生治療的模型服務現在正在逐步開展,并且取得了明顯的社會效應,比如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將3D打印技術引入骨科治療領域,進行了脊柱內的植物手術,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在國內首次將3D打印技術應用于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手術(TAVI),等等。目前國內生物3D 打印應用范圍較廣的子市場之一是在牙科行業,例如當前熱門的應用——3D打印牙槽骨。在短時間內,生物3D打印主要還是作為一些復雜手術的導航,簡化手術難度。但是現在的問題是,3D打印手術作為復雜手術導航或輔助的功能并不完善,尚未達到質的變化,像進行粉碎性骨折修復這樣難度的手術就很難做到。
記者:目前生物3D 打印發展迅猛,那么,在我國的市場前景如何?機遇和挑戰分別是什么?
劉靂宇:眾所周知,中國人口基數大,人口也在逐步進入老齡化。因此,對于醫療,特別是精準醫療的需求很大,如果生物3D打印技術成熟,可謂前景一片光明,因此不必考慮市場需求量不夠這一情況。可以說,生物3D打印技術的市場和商業應用比其他3D打印的應用更廣一些。因為人們(為了身體健康)是不計成本的。因此,只要技術過硬,能夠挽救人的生命,能讓病人的生活質量有所提高,基本上不需要過于擔心定價方面的問題。
目前,公眾對3D打印的概念已經有了一個基本的理解,接受起來困難不大,市場容量也很大。這是我經歷過的所有前沿技術中,外部氛圍最好的一種。另外,國家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計劃,比如《中國制造2025》就涉及到3D打印技術。當前,在精準醫療、智能制造的大背景下,對于開展生物3D打印的研究,前期孵化和后期產業化都是強有力的支持。生物3D打印技術可謂是處于前無古人的好時機。
但是機遇和挑戰往往是并存的。目前,公眾和政府都對3D打印有著很高的期望,如果3D打印技術不能像高鐵那樣盡快提供實質性的技術,讓人們能夠真切地感受到它所帶來的變化,可能很快會失去人們的信任和支持,或者像克隆技術那樣,發展熱度有所下降。一項好的技術,一定要對公眾產生實際的效果。3D打印技術,也一定要讓公眾切實感受到它帶來的好處,相應的,生物3D打印也必須為公眾帶來醫療水平和生活質量上的提高。
記者:目前中國生物3D打印的發展與國外相比的差距表現在哪些方面?國外有無成功做法或案例?
劉靂宇:我國在技術儲備上并不落后于國外發達國家,目前國內也不乏相關的人才,像國家“千人計劃”專家,都是從國外回來的精英,有中西文化融合的經歷和開闊的眼界。我國在技術上基本上是與國外同步的。
但是,3D打印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應用型技術,從整體上來說,我國和國外的差距還是很大的。
就技術本身來說,在科研方面,社會的氣氛比較激進,能靜下心來做好原創技術的心態不夠,從事科學和技術研究的人員應該具備務實的態度,不浮躁,不冒進。另外,許多資源整合得不夠,科研單位和企業之間缺乏緊密的配合,存在碎片化的局面,缺乏凝聚力。生物3D打印技術涉及到方方面面的,技術和應用應該是無縫銜接的。
就其應用而言,一個產業的技術革命,必須要打破利益壁壘,讓科研單位和企業都能釋放活力,充分投入到這一場技術和產業革命中來。從國家層面來說,首先需要一個好的分配機制,其次要認識到不團結就會落后,落后就要挨打。如果科研單位和企業沒有決心,閉門造車或者僅是仿制別國的技術和產品,生物3D打印的發展就一定會出現瓶頸。
找到差距的同時,國外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可供借鑒。美國約翰?霍普金斯醫院的一個應用物理實驗室,為先天或者后天殘疾的人做智能假肢。約翰?霍普金斯醫院并非只是一個單純的醫療機構,它有自己的實驗室,有自己的科學家做基礎研究。因此,研究出的成果會及時應用于臨床,結合緊密。而在這方面我國發展得還是相對落后。我國需要形成企業、高校、科研院相互協作,互利共贏這樣一個生態環境。
市場熱的冷思考
記者:就技術層面而言,您認為生物3D打印發展的最核心的問題在于?這一問題您認為該如何解決?
劉靂宇:技術層面最核心的問題是材料,也就是具有生物兼容性、可復合3D打印原理的材料。這需要科研單位、企業研究對醫學更有用的新生物打印材料,不要單純追求廣度和短平快。另外生物3D打印還較缺乏有展示度、領軍式的醫學應用,這就需要有一流的技術來配合,做出具有彰顯力、而且能夠在一般條件下廣為應用的典范。同時,技術的應用還需要好的商業模式加以配合。
記者:“生物墨水”是生物3D打印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,不僅成本高,而且材料特殊,近期有報道稱外國科學家開發出含石墨烯生物油墨可3D打印神經元,是否可以理解這一問題或將得到解決?
劉靂宇:如果真如報道所說,這個成果是非常有價值的。但就我了解到的情況,報道所說的石墨烯生物油墨打印的并非神經元,而是構成神經元的支架,它能夠支持干細胞在里面生長,實際上充當的是一個平臺的作用。神經元是非常復雜的細胞,沒有任何技術能夠打出來,如果能打出細胞,就有可能打出組織,甚至打出人來,那是上帝扮演的角色。報道的內容和標題不是特別符合,文章中對該成果有更為詳細和科學的介紹。就如我所說的那樣,公眾也許看到標題會產生誤解,因此我在這里需要澄清一下。
記者:作為交叉學科,生物3D打印技術也亟須與不同學科進行交叉合作,我國在這方面做得如何?您認為該如何去搭建交叉學科的合作平臺?
劉靂宇:如今,任何一項技術的發展都應該是以人為本,面向公眾的,但是它核心的還是人才,生物3D打印技術有多種交叉學科的融合,比如說工程、物理、數學、信息、生物、醫療等等。在這種情況下,這項技術要做大做好,需要各方面的人才。就我了解到的情況,現在無論是科研機構還是企業,在這方面下的力度都不夠,比如現在都提倡復合型人才,但高校在這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。3D打印是一個新興的產業,對于企業來說,在招聘人才時要精準布局,有人才才有可能實現研發上的突破性發展。要打破這個僵局,還是要有人出來吃螃蟹。發展3D打印,需要搭建一個交叉學科合作平臺,即把一流的高校和一流的企業融合在一起,打造一個平臺,大家在這個平臺里交流合作。另外,還需要研究機構和企業一道打破技術和利益壁壘,在技術、知識產權和利益方面實現資源共享,這是目前的重點和難點問題。
記者:國內有學者提出“生物制造工程”的學科概念和框架體系,您認為這個設想對于我國生物3D打印的發展有何作用?
劉靂宇:這一設想有一定的指導意義,事實上這個概念由來已久,早在1998年“21世紀制造業挑戰展望委員會”主席J.Bollinger博士就提出了生物制造的概念。我國學者也于2000年提到了生物制造。概念雖好,但卻沒有實施起來。現在做的研究大多是碎片化的研究,沒有形成體系。對于一些有價值的概念或者設想,相關研究人員或者單位需要支持,但更需務實。具體落實到3 D打印的研制和推廣,不能紙上談兵。目前高校和科研院所培養人才的體制還較僵化,有時忽視了跨學科人才的培養;而企業生存壓力本來很大,所以沒有健全的人才培養理念,對實習生重視不夠。從長遠來看,這就需要科研院所、企業共同規劃,不排除建立一些政策“特區”,讓一些有想法,有行動力的院所和企業先行,達到旗幟引領的作用。
未來發展:步步為營,穩中求進
記者:在目前生物3D打印火熱的市場前景下,您覺得我國應該如何抓住3D技術大發展的浪潮,推動我國生物3D打印技術的產業化發展?
劉靂宇:國家需要不斷評估和支持一批具有潛力的對于3D打印的研究和應用,鼓勵科研院校和企業深度融合,向產業化方向發展。最重要的是,如果有資金和政策的紅利,需要不斷監督和評估,實行淘汰制,最終選出一批具有領軍意義的3D打印技術的研究機構和企業。
記者:康奈爾大學的胡迪?利普森教授曾提出一個“3D打印生命階梯”的概念,您如何看待這個說法?這對于生物3D打印未來的發展有何啟示?
劉靂宇:我認為這個概念提出了3D打印的最終目標和實現的途徑,把人類幾百年后3D打印技術發展的軌跡都規劃出來了。但是我認為,這個生命階梯的概念雖好,我們卻不必把目光投得太遠,生物3D打印目前能夠把每個階梯充實完善就很不容易了,因為每一個階梯都需要和許多技術進行無縫的連接和融合。和其他技術,比如機器人技術,信息技術融合一樣,生物3D打印的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,切忌好高騖遠。總的來說,這個階梯的概念是非常好的,它所闡述的關于生物3D打印未來的發展趨勢也是毋庸置疑的,但是我們必須著眼于當下,把每一步做好,精益求精。
記者:有報道稱,生物3D打印或將引發醫學新革命,您怎樣看待這個設想?生物3D打印或將為人類社會帶來哪些變革?
劉靂宇:每當一項高新技術出來,人們就會把它和新變革、新革命掛鉤,但是究竟結果如何最終還是取決于我們現在的努力,以及努力之后是否能夠實現這一設想。在未來,3D生物打印或許能讓我們生活得更健康,甚至改變我們的醫療方式。比如,配合3D影像和智能機器人技術,未來3D打印也許可以很快對于燒傷的病人進行組織修復,可以為戰場上的士兵提供傷口定制的止血修復,甚至可以讓美容整形手術標準化,定制化。這些都會是革命性的進步。
記者:對于生物3D 打印未來的發展,您有何建議?
劉靂宇:將來研發的生物3D打印技術,無論是可降解的組織框架還是活體組織細胞。盈利模式依靠耗材和打印服務會成為主流,設備銷售只是輔助我們市場鋪面和營造產品宣傳。前期,線上主要通過代加工和服務平臺迅速提高我們的品牌知名度。線下則可以通過醫院和政府進行宣傳,開辦免費體驗店和醫療支援,擴大產品影響力,對現有醫療技術的實用性幫助和國民認知度。后期,等品牌影響力成熟后,可以要針對普遍性的醫學難題,研究出新型具備自足知識產權的生物3D材料。
編輯:Kris
